《清华元史》是除《中国学术》外,由恢复后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另一个重要学术园地。经过一年多的周折和艰辛,现在终于可以将这一册创刊号呈现在读者诸君眼前了!
蒙元史研究与老清华国学院、老清华历史系的因缘,不可不谓至久且至深矣。王国维甫入清华,其治学重心即转向蒙元史而成就斐然;国学院期间的陈寅恪,写作授业多流连于“塞表殊族之史文”。二老相与继唱迭和,曾分别萌蘖续写“元史考异”或创制“新蒙古史”的心愿。邵循正译注的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等名篇,虽因手稿焚毁于抗日战火而未得面世,但他在归国最初十多年内克勤致力于元史研究与教学,仍足为老清华历史系平添一道闪亮耀眼的学术特色。中国目下健在的最高龄一代元史名家,或出其门下,或有亲灸其教之幸。
可能也正为了有这样一份因缘在,我们从王国维遗墨中选用他的行楷拼合而成的刊名题签,竟显得那么笔势劲媚、骨气洞澈,简直好像...
《清华元史》是除《中国学术》外,由恢复后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另一个重要学术园地。经过一年多的周折和艰辛,现在终于可以将这一册创刊号呈现在读者诸君眼前了!
蒙元史研究与老清华国学院、老清华历史系的因缘,不可不谓至久且至深矣。王国维甫入清华,其治学重心即转向蒙元史而成就斐然;国学院期间的陈寅恪,写作授业多流连于“塞表殊族之史文”。二老相与继唱迭和,曾分别萌蘖续写“元史考异”或创制“新蒙古史”的心愿。邵循正译注的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等名篇,虽因手稿焚毁于抗日战火而未得面世,但他在归国最初十多年内克勤致力于元史研究与教学,仍足为老清华历史系平添一道闪亮耀眼的学术特色。中国目下健在的最高龄一代元史名家,或出其门下,或有亲灸其教之幸。
可能也正为了有这样一份因缘在,我们从王国维遗墨中选用他的行楷拼合而成的刊名题签,竟显得那么笔势劲媚、骨气洞澈,简直好像是他专门为本刊写就的!
必须指出,《清华元史》虽以“元史”命名,惟全然不为蒙元史的对象范围所拘限。盖举“元史”之名,实乃用以指代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及边疆史地之全部领域也;换言之,本刊殊以多民族视角下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初旨。这样做,正可反映出中国民族史学科之现代转型过程里的一个显著特点。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道咸以降的“西北舆地之学”向从事边疆民族史的现代研究范型的转变中,洪钧和他的《元史译文证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无与伦比的。经过他的译介与阐扬,中国学者见识到欧美东方学以中国民族语文及域外资料与汉语文献比勘互证的新路径、新成绩,纷纷争而效仿。蒙元史研究因此成为代表着中国边疆史地学术新潮的首开风气的显学。
举蒙元史以概指“边陲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有另外一层强有力的理由。在中国各民族历史文化多样性的光谱上,汉文化与蒙古文化恰好分别位置在它的两端。当拉铁摩尔把中国内陆亚洲各边疆民族的生态环境简约为蒙古草原-新疆北部的草原绿洲-南疆的沙漠绿洲-西藏的高寒山地绿洲这样一种“变形”序列的时候,他力图解答的,就是蒙古文化为何更容易与上述各族文化具有不同程度互融性的问题。因此他断言,“东自满洲的混合型地理环境,西至中国突厥斯坦的沙漠和绿洲,乃至西藏寒冷的高原,起源于上述各地区的那些社会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完全可以说是基于蒙古草原历史的一系列变形。”以此言之,设若中国民族史确然存在着某种典型性,其惟蒙元史足以当之欤?
清华国学院曾经的辉煌,是让后世永远心往神追的一段奇迹和佳话。而老清华研究“边陲中国”的学术遗训,尤其应当是由我们毫不犹豫地拿来继承发扬的宝贵家当。其中至少有两点,最值得我们再三再四地回味和重温。
在探讨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的本国学者中,老清华诸大师无疑都属于那个不但最早具备了国际学术眼光,而且能摆脱完全依赖西文绍介而直接利用相关民族语文及域外语言资料的前沿学者小群体。正是由于这一进步,本专业的叙事才得以从边裔志、藩部要略之类传统历史编撰学的体裁之中,逐渐转换出真正名副其实的边陲地域史、边陲族群史或族群关系史新模式。这里所关涉的,不仅是从何种语文的文献史料出发去形成叙事的问题;它背后隐含的,实际还有一个应不应当突破单向度的中心视角,更多地留意于从多民族中国的视角去考察边缘人群、边陲社会历史与文化的问题。日本学者羽田亨在1917年就提出了被后人概括为“当地语文之史料第一主义”(“現地語史料第一主義”,gentigo shiryō daiiti shugi)的见解。从那时起,日本的内陆亚洲史研究花了五六十年时间,到1960年代末才基本实现上述主张。就整体而言,中国学术界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尚待时日。在今天,追随老清华的精神表率,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奋力抉破相关民族及域外语文技能的难关,而且也应当重视和掌握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研究中其他那些不可或缺的“钥匙”,诸如解读多语种古文献时的审音与勘同知识,分子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概念与方法等等。
老清华时期治边疆史地之学的前辈们,多以考据功夫受人推崇。但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的,不止是那种“客观”、“科学”与“价值中立”的治学原则而已。在他们从中国文化内部所从事的对自身传统的反省、清理与扬弃背后,饱含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前途运命、对根植于中国文化之基本价值的深切关爱与持守。由是,他们使自己的学问俨然区别于洋人的“汉学”或“中国研究”,后者往往倾向于把中国文化当作纯然客体性的解剖对象来处理。这一点在当今形势下显得尤其要紧。因为“边陲中国”的重要性,在今后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紧迫、越来越需要以一种更带全局性的新思维予以考量。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目标,追求的往往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理想,即以汉文化去覆盖国家的全部疆域。这种历史意识的残余影响,与误以为现代化终将促成一国文化全盘均质化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夹缠在一起,正在并且将会更进一步地损害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根本利益。我们当然不应该奢望,边疆史地之学可能直接回答未来的中国民族关系将会提出在我们面前的任何现实问题,但它理应使我们对现实的关怀臻于某种更平衡、更理性,也更加智慧的思想境界!
以上就是我们寄托于这份杂志的美好的愿景。它最多不过是一脉涓涓的细水。殷切期望它会汇入即将到来的重建中国文化的巨流之中。我们正走在前人以筚路蓝缕的心血为我们开出的路上。为了不辜负前行者,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紧接着他们往日的业绩,用力去铺就通往将来的更踏实的路。
 清華元史(第一輯)txt,chm,pdf,epub,mobi下载
清華元史(第一輯)txt,chm,pdf,epub,mobi下载 首页
首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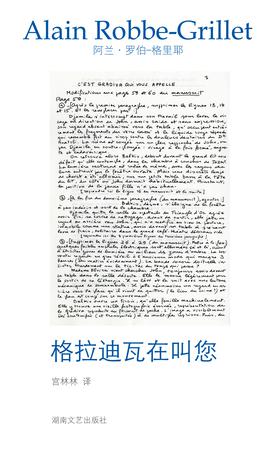



一种全新的角度切入
期待内容,好想赶紧开始看
这本书真的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同时细微处又有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