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无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残酷的真相告诉世界。”
《一辈子的战争》记述的是一场离我们时间最近的战争中的人与事。1985年,李玉谦二十三岁,是一名战地记者。这一年,中越边境防御作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
1985年11月25日晚,云南老山主峰脚下的磨刀石,他与战士们一起喝了出征酒,然后,用他的摄像机记录下那次战斗。
二十七年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那场酒,那群人,那次战斗,那场战争,李玉谦有意回避。他从不看战争片、战争小说,从不跟七连的人联系。他希望忘了那一切。
《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是云从龙先生整理的一个不知名的普通人的日记。如他所述:
庚寅年十二月十三(2011年1月16日),一位朋友与我闲聊,说起他新近收藏了一本日记,其中记叙了一个寻常家庭一年多的日常起居。出身社会学科班的我,立即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问他可否将日记本借我观瞻,他欣然允...
“你如果无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残酷的真相告诉世界。”
《一辈子的战争》记述的是一场离我们时间最近的战争中的人与事。1985年,李玉谦二十三岁,是一名战地记者。这一年,中越边境防御作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
1985年11月25日晚,云南老山主峰脚下的磨刀石,他与战士们一起喝了出征酒,然后,用他的摄像机记录下那次战斗。
二十七年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那场酒,那群人,那次战斗,那场战争,李玉谦有意回避。他从不看战争片、战争小说,从不跟七连的人联系。他希望忘了那一切。
《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是云从龙先生整理的一个不知名的普通人的日记。如他所述:
庚寅年十二月十三(2011年1月16日),一位朋友与我闲聊,说起他新近收藏了一本日记,其中记叙了一个寻常家庭一年多的日常起居。出身社会学科班的我,立即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问他可否将日记本借我观瞻,他欣然允许,第二天便从家中带来了。那是一本三十二开淡黄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看上去几乎全新,只是放得久了,略略散发出一点纸张的霉味。展开扉页,上面用毛笔写了一句赠词:“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落款为“采选科工委赠,一九六七年元月”。凭借这一点,我初步判断这是一本有些年头的笔记本,其本身的历史至少有半个世纪了。时隔这么久,尚能保存得如此完整,实在难得。最为要紧的是,它是一本私人日记。窃喜之余,我立即翻开内容去看,想不到的是,日记并不是写于1967年,而是写于1991年,也就是说,这是一本用五十年前的笔记本在二十年前写下的日记。
朋友见我爱不释手,生怕我有夺人所爱的非分之想,连忙要收拾回去。我请他通融一下,借我将所有内容复印下来,原本一定会还给他。我用三天复印了所有的日记内容,自行装订成册,同时将原物奉还给主人。此后,只要得来闲暇,我都会翻翻这本写于二十年前的日记,仔细揣度日记主人当时的生活点滴和音容笑貌。
在我看来,这本日记所记载的内容虽然都是些日常起居,生活琐事,但比之现已出版的诸多名人日记来说,又有别样的价值。研究抑或观察一个社会的变迁,除了关注当时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心理脉络,更重要的是要摄取民间乃至市井百姓的心理切片。可惜的是,前者大都通过各种途径或多或少保留了下来,而市井百姓对于世相人文的态度,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几乎整体性淹没。我手上这本日记,正好能让我们看到二十年前一位普通公民对于生活和世事的种种态度。体会她的喜怒哀乐,也是在体会1990年代整个社会的喜怒哀乐。
《巴黎画派中的黄皮肤》介绍日本画家藤田嗣治的生涯与艺术。
他留学法国,成为巴黎的宠儿。当日本一方面加快法西斯化步伐,一方面对中国大陆的渗透和侵略开始升级时,他回国,前卫艺术家成为“彩管报国”的代表人物。在军部所谓“画家当以画笔为战时做贡献”的号召已成既定国策的情况下,艺术界的“报国体制”瓜熟蒂落,甚嚣尘上的“彩管报国”口号,作为赤裸裸的战争意识形态被固化,嗣治开始创作战争画,获军国主义高度评价。
对战争画,他有自己的一套诠释:
绘画可直接有用于国家,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抚慰国民的绘画与使国民强健的绘画,二者是有很大差异的。世间仍有人在说战争画不是艺术,或者持别样的看法。在战争画领域,做出出色的艺术品并非不可能,而这恰恰需要我等去努力创作。日本画中的战斗画素被认为是极难的技艺,可事实上正由日本画家的同仁们在努力进行到底。一定能出现卓越的日本画的战争画,我对此无比期待。
日本战败,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拉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罪犯公审的序幕。战犯追究不仅局限于军、政两届,迅速波及舆论和美术界,锁定并制裁战争协力者的声浪开始升级。舆论界展开了关于“美术家节操”的论战,一部分战时受到压制的画家及日共系的普罗艺术家走到前台,口诛笔伐,声讨“画坛战犯”。
最终,当局做出了藤田嗣治不属于战争责任者的判断——一千零六十七名战犯名单中,无一名画家。在战犯嫌疑问题上,嗣治终于平安“软着陆”。他就此永别日本,客居法国,皈依宗教。
临终的时日,画家田渊安一特意从巴黎赶到医院,开口问了他那个在内心盘桓已久的问题:为什么要画战争画?
画家并未正面回答“为什么”,嗣治断断续续地说:“战争确实是相当悲惨的事。你看一看那些画就会明白,那里面没画过一个将校。送死的士兵最可怜,我画的只有士兵。”
2010年2月8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施崴青小城在夜色中已沉寂多时,三十八岁的电台女主持人克劳迪娅终在寓所等到心上人的到访。在他们长达十一年的感情生活里,有过甜蜜与和美的时刻,也有过争吵与波折。这晚的共度时光似乎并不愉快,凌晨时分,男方拂袖而去,女方流泪报警,称遭到了男友的性侵。她述明:“当晚双方发生争吵,缘由在于她再次提及对方隐瞒的风流韵事。男方揪住她的头发,用一把切番茄的厨刀抵住她的颈项命她闭嘴,随即将她扔在床上实施了强奸。”
爱在顷刻间崩塌,诉讼战争旋即到来。
《德国的世纪诉讼》介绍的就是这一案件。风云变幻、迷雾重重、观者如潮、议论纷涌……两年间,围绕着卡赫曼涉嫌强奸案,德国媒体进行了长篇累牍的追踪报道,德国各级法院也不得不一再对此发表意见,范围不仅涵盖刑事诉讼领域,而且也拓至人格权保障、司法公开与媒体自由等议题。
行使“第四权力”的媒体对刑事诉讼报道的最低界限何在,成为信息社会下值得关注的问题。
 读库1203txt,chm,pdf,epub,mobi下载
读库1203txt,chm,pdf,epub,mobi下载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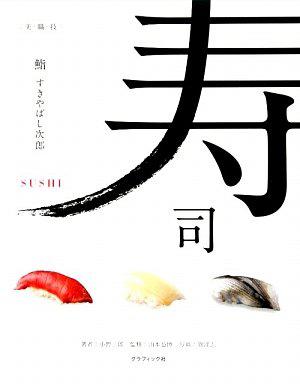

结合当下分析得也通俗明了易懂
还没有看完
还没看
为我提供了一个解看历史和现实的全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