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現代(主義)」一詞已充斥於文化論述,乃至於日常語言的今天,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校區的伊哈布.合山教授收入本書的十篇論文,彷彿一次次精采的批判性演出,構成了理解文學後現代主義的最佳參考依據。作為後現代主義最早的年代紀學者之一,哈山對這個術語的得以逐漸被接受,貢獻可能超過任何其他批評家。本書鋪陳作者本人對後現代主義的思維發展歷程,探索這個概念所經受的各種磨難與考驗,並檢討有關的論辯,足以讓讀者領受一個文化進行自我了解時深沈、豐沛的一面。
-----------------------------
導讀
.廖朝陽(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在晚近有關後現代的理論探討中,哈山所佔的位置並不十分重要。主要的原因是即使到了 80 年代,哈山還是堅守某種文學本位的「沈默批評」的立場,與主要辯論中各種學科知識與政治立場相互激盪的鬧熱氣氛顯得格格不入。這並不是說,哈山的討論毫無價值;相反的,透過哈山的呈現,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值得檢討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與某些後現代理論的基本觀念仍然是息息相關的。
我必須先就「沈默批評」的意義,稍作說明。沈默批評是哈山所謂沈默文學的延伸。在哈山的心目中,西方文學的主流是「從形式走向反形式」,而形式的作用是透過作品語言與藝術規格的操演來保證意義的傳達,所以走向反形式也就是走向沈默,切斷語言和現實之間的關係,把文學變成一種高度自律的,內顯(imminant)於文字當中的半神祕經驗。同樣的,哈山心目中的理想批評也保有高度自律的傳統承遞(從文藝復興到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它的發展動力來自某種內在的規律。所以晚期的哈山特別強調批評或文化理論必須抗拒來自非文學部門的解釋規範,避免沾染特定的政治立場,不向任何意識形態靠攏。這個立場代表了人文主義傳統的一種典型。可以想見,在一般文學研究者當中,哈出的說法還是具有相當代表性的。
如果我對哈山立場的解釋可以成立,這裡面至少牽涉到兩個問題。其一,文學研究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這種觀念代表的是學科分立的韋伯式現代理性,豈不是大大違背了哈山自己強調的反目的,反連續,反主體的後現代精神?其二,哈山並不否認後現代是產生於「西方社會和它的文學」中的現象,甚至有文學思潮是後現代社會「一個獨特的、精英的方面」的說法。那麼語言文字顯然並不僅是以沈默、憤怒、抗議來面對(規格化的)外在環境,而是在一定的層面上準確的反映,或者說模擬了其他社會、文化部門的現實。
這兩個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為文學的兩種發展方向的衝突:文學應該秉持抗議精神,嚴守內在的規律,走向社會狀況的對立面,還是接受下層結構的決定,撤除界限,回歸現實的同質面?或者說,文學應該成為社會的監察院,還是社會的存查院?第一種方向本於求真實、求自主等原則,當然具有強烈的現代精神,第二種方向則似乎具有後現代平淺化、反等級、反創造的意味。這裡並不是說,哈山的講法有矛盾:後現代是現代的延伸或修正,或者後現代與現代可以並存,或者兩者皆是,本來就是哈山一再強調的基本立場。我也不想引用辯證關係、相對自律之類的說法,來為兩種傾向強作連繫。另外,這也不是語言或翻譯意思不準確所造成的問題,雖然我們必須記得,postmodernism具有從後現代主義、後現代現象到後現代症等等的多重涵義。這裡想指出的重點是:哈山以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抹除」了這兩種方向的衝突。不是化解,也不是調和,甚至不必動用互補、延伸等觀念;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忽然發現,監察院其實就是存查院。
或許我們可以對哈山的思考路線作一個外繫式的說明(雖然這不合強調內顯的後現代精神)。在一個理想的社會裡,真偽、善惡是十分確定的,並不需要有一個專責批判或異議的部門存在。而當這個涵括社會整體的確定性喪失的時候,文學以及其他現代學科就從這個整體獨立出來,接收了確定意義的責任。也就是說整體所失去的確定性,是以窄化、深化的方式,由部分收回來。哈山顯然認為這個分裂、離散的過程一旦開始,就很難終止。所謂一切整體都是專制、極權,便是說整體的意義是用確定的規矩來掩蓋不能確定的真實。社會整體的價值既然難定,文學整體、作品整體、作家整體等等何能獨善其身?任何由整體獨立出來的次整體遲早都會被原來的整體同質化而落入被懷疑的命運。於是不確定的範圍愈來愈大,提供確定功能的對立面則愈來愈緊縮。可以想見,這個過程發展到最後,扮演對立角色的自律部門終會完全失去存在空間:不斷懷疑的結果便是懷疑者本身也受到懷疑而消失。對立批判的精神(「創造意義的欲望」)不斷從整體離散出來,終至無所依歸,只能像無廟可棲的散仙那樣,一切存查而轉入意義的嬉遊。這就是所謂「逍遙離散」(ludic dispersal)了。
哈山顯然不滿意這種歷史告終、意義也告終的結局,所以在晚期改採實用主義的多元論,要在局部實況中重建確定性,但同時保存由各種實況的差異所構成的不確定性。這等於是說,後現代精神在到達否定一切的終極困境之後,必須回頭轉向,重尋確定的意義。這裡的問題是,意義分裂、離散的過程是由現代精神的內在規律所推動的,它一旦逆轉而重走聯結、聚合的老路,這內在的動力是不會因為理論家的主觀意志而停留在某一「局部」層次的。從哪裡喪失的確定性,就會從哪裡找回來:既然某些局部實況可以有整體的意義,那麼為什麼不能把社會整體也當成是一種實況,賦與它確定的意義?理論操演固然可以就實況的層級作種種(經驗論的)分辨,但只要理論本身是自律部門的一部分,它所內含的可能性終究會按孔恩式(Kuhnian)科學典範的發展規律,獲得實現。這等於是把後現代反統合、反整體的漂遊觀又重新還原為超然客觀的現代精神。有朝一日,我們又會發現,原來存查院也可以變回監察院。
這種以後現代面目出現的現代精神,在實用主義多元論的立場中已經可以看出端倪。表面上看,實用主義既保全了後現代尊重局部實況的精神,又可避免陷入虛無空洞的反現代的嬉遊,似乎是後現代理論的合理歸宿。其實,實用主義常被認為是一種過度保守的主張,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多元論的前提是:此狀況的真實與彼狀況的真實不同,但可以並存(一個典型的說法是:「我不同意你的說法,可是我支持你說話的權利」);然而多元論既然是以理論的形式出現,這個前提往往會一般化而變成這樣:此狀況的真實與彼狀況的真實可以並存,但不能相同(「我支持你說話的權利,可是不管你怎麼說,我都不贊成你的說法」)。也就是說,多元論者所占的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地位;他可以決定各種實況的界限,判斷由其中確定出來的意義是否合法,然而他自己卻是不受任何實況限制的超然旁觀者(只有他才能決定別人有沒有說話的權利)。在哈山討論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時候,這個傾向表現得特別清楚: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在過去的實況中產生出來的,所以不能把自己當成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其實,這是非常形式化的規矩;真正值得考慮的應該是:過去的實況與當前的實況有沒有一些相通的因素,可以為後來者借鏡?馬克思主義者顯然是認為有。那麼反對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針對事實來討論各種實況之間可不可以相通的問題,而不是跳出實況,斷言所有追求普遍性的理論都是意識形態。這裡哈山的表現多少會令人懷疑,所謂實用主義的立場是否就是要切斷實況與實況之間的連繫,以多元存查的方式達成社會體制的超穩定化?
透過離散與聚合的循環變形,哈山抹除了現代與後現代的差別。然而,如果實用主義就是最後的結果,我們也許應該重新考慮,這套解釋是否有什麼遺漏。我的看法是,在現代精神裡面,文學或其他文化部門具有批判、理議的功能,應該不是問題。問題在:批判而必形成批判部門(監察而必成立監察院),就開啟了批判走向反批判(監察走向存查)的路程。不管是確定性或不確定性,都不可能只存在於某一特定的部門,而是散布在社會整體的各個部分,接受各種現實狀況的制約與決定。文化部門的獨立是現代學術發展過程中的事實,但這並不是說,獨立的結果就必然會產生一個形態確定,負有固定任務,與現實條件完全脫離互動的自律體。哈山既然認為西方文學有一主流,必然是要就文學的內在規律來發展他的思考。結果,社會整體並沒有向文學所提出的對立面理想演變,反而是文學本身(或者說哈山的敘述)不得不按內在規律走入自己的反面。
如果說反本質是後現代的一個特徵的話,那麼這種部門獨立,角色獨立的思考格局恰恰是陷入了文學本質的舊套。但是我們也常聽到(不限於哈山),後現代就是反這個,反那個,或者是後現代具有三點特徵、五點特徵等等的概括性說法,這一類的「定格畫面」難道不也是有關後現代本質(或內在規律)的,非常確定的描述嗎?這些都是因為形式概括而造成意義必須走入反面的例子。後現代主義者當然也可以有「有時反有時不反,才是真反」之類的詭辯,但是要真正解決問題,恐怕由內顯走向外繫,根據實況引入形式、規律之外的決定因素,才會有更具建設性,更實用的結果吧。
 後現代的轉向txt,chm,pdf,epub,mobi下载
後現代的轉向txt,chm,pdf,epub,mobi下载 首页
首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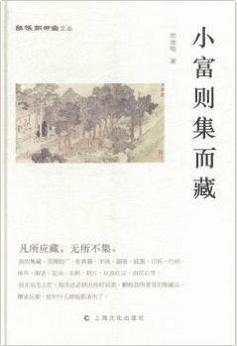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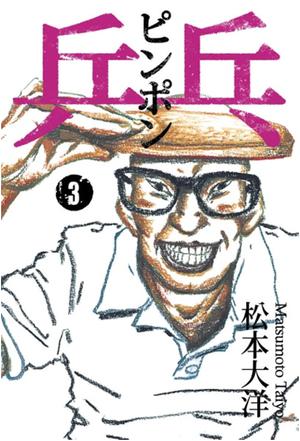

初中生最应该看的
很有收获的
让人叹为观止。
很好,家人喜欢,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