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的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
 云南三村txt,chm,pdf,epub,mobi下载
云南三村txt,chm,pdf,epub,mobi下载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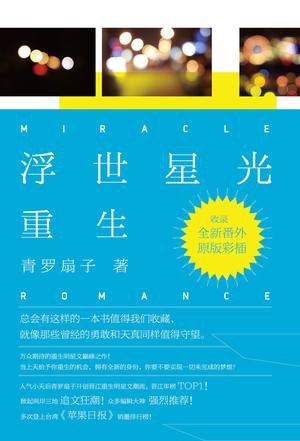
非常值得一看的好书
让人叹为观止。
作者让我脑洞大开
好评!有一本神奇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