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儿我要插一段写于2001年6月4日深夜的报告节录,有关当天中国证监会稽查局稽查三处两位人员听证我的情况,内容主要涉及2001年我所写的《基金黑幕》(参见第一章中的有关介绍),报告的对象是中国证监会的领导。
这份颇有卡夫卡小说风格的报告记录耐人寻味之处颇多。由于我多年来在媒体工作,所以要我配合调查的有关方面也有一些,我没有一次不主动配合他们工作的,有关方面最后都比较满意。可是,我从来未曾想到中国证监会的人员竟如此角色错位,在调查中,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个监管人员,而对方是被监管对象。中国有句俗语叫做“皇帝不急急太监”,也许吧。我早年就在上交所工作,后来又被借调至中国证监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一直比较在意研究监管原则,可能来调查的证监会人员也没精神准备,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调查开始了:
2001年6月4日,在上海证管办的二楼会议室,我接受了稽查局三处两位同志的调查,一位是副处长L先生,另一位是担任记录的W小姐。
大家开始接触时,都比较客气,我介绍了《基金黑幕》的写作背景、内容和目的。我认为这篇文章主要是客观的研究,对基金行为的描述分析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基金或者说机构投资能否稳定市场,从上交所的报告来看,内地基金的行为难以证实机构投资者稳定市场的结论,这属于学理上的探讨;第二部分,基金利用公告的公布日和截止日期的时间差做文章,这属于自利动机,是否道德是其次,但我们建议把这种时间差缩短,有利于投资者获得准确的信息;第三,上交所报告显示出的基金“对倒”行为,由于这样可以促使成交量虚假,误导投资者,属操纵行为,所以《证券法》明令禁止。
另外,上交所报告的价值在于基础数据,采用的统计方法十分简单,不存在统计方法有误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上述这些推论解析是完全可以通过基础数据得出的。
让我很快感到问题不对的是,L先生没问两个问题后,突然示意记录员停笔,他说“我们岔开来谈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下列问题不做笔录。
L谈了对《基金黑幕》的看法。我回忆大致如下:第一,中国证券市场还很年轻,违法违规在所难免;第二,美国市场也是如此,那儿的问题还要多;第三,要尊重“国情”,这种事不单在股市中有,中国别的市场上也多得是;第四,稽查局人手少,有心无力。
我感到很惊异的是,这种为基金辩护的口吻竟出自一位应客观公正的稽查局同志口中。我只能一一作答:第一,中国股市是很年轻,但年轻并不代表可以违法,至少我们可以努力;第二,美国市场20世纪初违法的事情的确不少,但现在已没有这样盛行了;第三,国情要讲,但金融市场也有一些普遍规律性,比如中国证监会与美国SEC至少在初期的架构上很相像;第四,你们稽查局人手少,正需要媒体的协助与监督。
我边说边感到很尴尬,因为我感到自己与L的角色在错位,坦白地说,我觉得我在普及为什么今天中国股市需要规范的知识,这本来应该是他们工作的基本要求。
L突然客气地说,不打不相识嘛,也许今后咱们会成为朋友或者成为陌路,都没关系嘛。
我又一愣,忙说,我没有和你“打”的意思,我是在配合你调查啊。
在其后的两个多小时中,L同志并没有对《基金黑幕》一文中所提的有关基金行为内容希望我作出进一步的阐释,而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基金黑幕》凭什么做到客观公正,凭什么在“编者按”中得出基金违规违法的结论等等。
在提问后,我作出的回答,L同志总是不满意,结果变成了辩论,而且他不时“岔开来”,让我分不清他是听证提问还是诱导我回答他想要的答案。我据记忆将两种形式所述如下:
L:你在写这篇文章时,凭什么认为上交所的报告是真实的?
张:我已经说过,它的数据是不可能造假的,因为根据我多年在上交所和从业的经验可以判定这点。
L:你为什么不去核实,没有核实的报道是客观的吗?
张:在美国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也没有向尼克松去核实,因为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L:我不跟你谈论美国,这是中国。
张:我们无法核实,是因为这有可能被人认为涉嫌干扰稽查工作甚至涉嫌窃取市场情报。
L:(后来又绕回来)你为什么不作核实?
张:我再说一遍,第一,我相信《财经》杂志以往的原则和报道,我信任它;第二,根据我十年的从业经验。
L:你凭什么说这篇文章是科学和客观的?
张:有事实依据就是科学的,当然它需要事实检验。
L:你们取得报告作者的同意吗?在不同意的情况下,文章能够发表吗?
张:(心想,这确实是基金联合声明后,我们考虑到如果要接受诉讼的话,对方律师必然要问的问题,因为它是最有争议的一点。L怎么越来越像基金的律师呢?)我们没有照发原报告,只是报告解析而已。
(注:我没说的是,即使作者愿意授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岂不是害他吗?)
L第二个让我缠绕不清的问题是:凭什么《基金黑幕》的“编者按”最后认定基金违法违规?
张:这是编辑部的按语,我无权过问。
L:在稽查局没有认定这种行为时,杂志就可以(擅自)作出决定吗?
张:可以,当然用“涉嫌”可能更好一点。因为类似的说法其实早已在圈子里流传,获得报告后,我们认为这里已有事实证明违背了《证券法》。既然违法,我们就可以认定。
L:你认为可以认定?
张:对。美国媒体在1994年根据两位学者的报告指控纳斯达克的坐市商有市场操纵行为,1997年美国SEC也认定了这一点。
L:这是中国,不是美国。
张:你们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同志也曾发表讲话,欢迎媒体配合监督市场。
L:我们现在是在对《基金黑幕》就事论事。
张:我对你们的听证立场表示怀疑。
L:你认为发表《基金黑幕》是负责任的吗?
张:负责任!杂志社既然发表了文章,当然就得负责任。人们可以对这种认定提出质疑,基金声明就是如此。
L:就凭报告的这些数据就可以得出违法的结论?
张:可以,我刚才也已经解释过了。
L:你(还是)认为这是可以认定的,在稽查局没有做出认定之前?
张:可以,我再说一遍,我认为在《基金黑幕》发表之前,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已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基金黑幕》的认定,我们认为违法行为已危及市场的发展。
L:这是你个人的看法。你不知道《基金黑幕》给市场带来了多大的震荡,这是负责任的吗?
张:L处长,L处长(我想提醒他的职责是稽查),你难道不认为《基金黑幕》出台后对中国股市的规范作用吗?
L:我承认。
张:我们丝毫不想越权,也没有不尊重证监会的意思。《基金黑幕》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投资者想要证监会有个说法。杂志只是一个媒介,它不可能有你们的权威性啊。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L此时突然勃然大怒,大声喝道:“什么L处长L处长,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今天你是来接受调查的!”
双方沉默……
L:我要问你,中国证券市场的最终认定权在哪儿?
张:法院。(此时的L忽而是个律师,忽而是个稽查处的官员,我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尽管他一开始时出示过工作证)
L:(忽然苦笑)你要这样说,我就无话可说了。
这时L递给我一份有关媒体披露信息的规则,在里面赫然写着如果报道不实要触犯刑律等等。我是个证券媒体工作者,类似的规定当然是很熟,但此情此景明显是让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客观、不真实,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L:我再问你,中国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的最终认定者是谁?
张:(我沉默良久,心里非常难受,我此时真的不想说是中国证监会,因为我已迷失于中国证监会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究竟要干什么的困惑中)中国证监会。
注意,这时L提出的问题又诱使我必须回答他的所谓正确的问题了。
L:那么,到底是中国证监会还是《财经》杂志有这种认定权?
张:中国证监会有最终认定权,《财经》杂志有初步认定权。中国证监会有权否定《财经》杂志。
L:(自我解嘲)真是搞文字工作的,真会玩文字游戏啊。
张:我不认为这是文字游戏。但我不想讨论,因为我不知你什么时候又“岔开来”,或什么时候是稽查员,讨论是互相要问问题的。还是你问吧。
关于文字游戏问题,我还想到L同志在我的文章中找到基金净值游戏的一段话。
L:你凭什么说基金是“欺诈”,难道游戏就犯法?
张:你拿给我看看。是你搞错了,上面写着“欺瞒”,和欺诈是两回事。
L:中国证券市场的执法主体是谁?
张:中国证监会和下属机构。
L还很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获得这个报告的。
L:你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报告的?
张:《财经》杂志编辑部。
L:我问你是谁?
张:记者李菁。
L:这份报告的格式是怎样的?上面有没有作者的名字?有没有公章?有没有单位名称?
张:我不知道。我接到的报告是简单的文本格式。
L:你们是怎么知道报告的作者的?
张:《财经》杂志社告诉我的。
L:你就相信了?
张:相信。
L:那份报告呢?可不可以交给我们?
张:没有了。风波发生后,我认为也许会有麻烦,也就不必保存了。
L:你们知道《财经》杂志的背景吗?
张:不知道。
L:我也知道你往《财经》杂志社身上一推,什么问题你都不会回答,但程序上我还是要问一遍。尽管说只写了一部分,但文章上合署你和李菁两个人的名字,所以还得文责自负,知道吗?
张:知道,我对《基金黑幕》负责。
L:那么,在《基金黑幕》中有那么多的“据说”,这是不是客观公正?
张:这是通行的报道体例。当然,如果把我的解析部分和她的文章分开来,解析是解析,报道是报道,这样会更协调些。我对《基金黑幕》负责,但这部分还是问她比较好。
L:我认为这些“据说”可是“致命”的。
张:对不起,我认为这不是“致命”的。
L:我用这个词可能“不恰当”,但……
张:报告本身的解析是“雪中送炭”,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报道可能是编辑部考虑更符合媒体的生动性,是“锦上添花”,如果不能“锦上添花”,也没问题。
L:你在解析部分提到了拉高股价、庄家可能赚到一倍利润。你有什么证据?
张:是推理,也是圈子里的看法。文章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要有数据支持的,尤其是在股市中,我无法获得庄家的记录。这需要你们稽查局核实。
从下午2:30至5:00,我们反复缠绕的问题就是这些反复问反复回答的内容,最后记录经双方审阅,签字。记录部分我认为是真实的,但明显没有把当时许多“岔开来”的话记录下来,而我认为这与记录员无关。因为很多“辩论”与L同志的说话确实不像听证。下面是我们最后的交谈:
L:我也是按程序走,不必介意。我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客观嘛。事实上,我自己都没看过上交所的那份报告。
张:(大惊,语塞)你没看过这份报告?唉,我建议你看看。
L:你刚才只要将那段“编者按”的认定问题推给杂志社就可以了嘛。我也是回去给领导看的嘛,总得有个交待吧。你放心,结论会对你有利的,你只写了解析报告的那部分嘛。我可是为了你才专程到上海来的啊。
张:如果你们如此这般的听证是在《基金黑幕》文章发表不久,我可以理解。但是中国证监会已公开宣布基金确有违法违规行为,而且许多基金的年报也承认这一点。而现在你们又开始立案调查《基金黑幕》的客观性,我难以理解。我不知道你们哪个代表中国证监会。
至于我为什么要坚持媒体的权利,这是因为市场利益的力量太强大,与此相比,媒体非常脆弱。如果我们不坚持这种权利,媒体的公正监督作用很快就会消失的。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由于L同志的问题反复缠绕,我只能对我们的对话进行一些编辑,让人有个头绪。而且,这不是录音记录,个别语句可能有些微出入,但不会妨碍其准确性。由于多年来的记者训练,加上回来的五个小时后,我就迅速将它回忆下来,相信比较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中国株式市場の真実―政府・金融機関・上場企業による闇の構造txt,chm,pdf,epub,mobi下载
中国株式市場の真実―政府・金融機関・上場企業による闇の構造txt,chm,pdf,epub,mobi下载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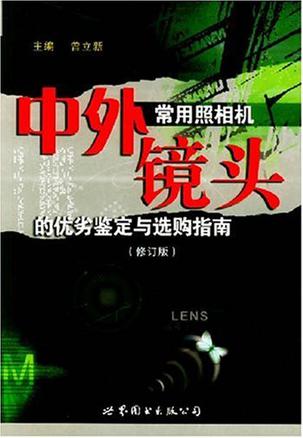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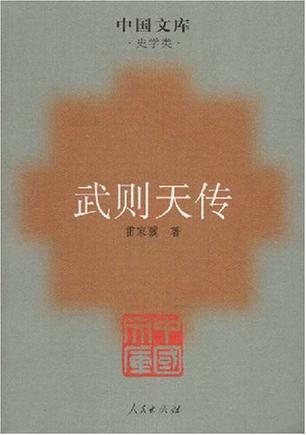
这本书真的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哈哈哈哈哈哈
值得一看
新书,看看后追评